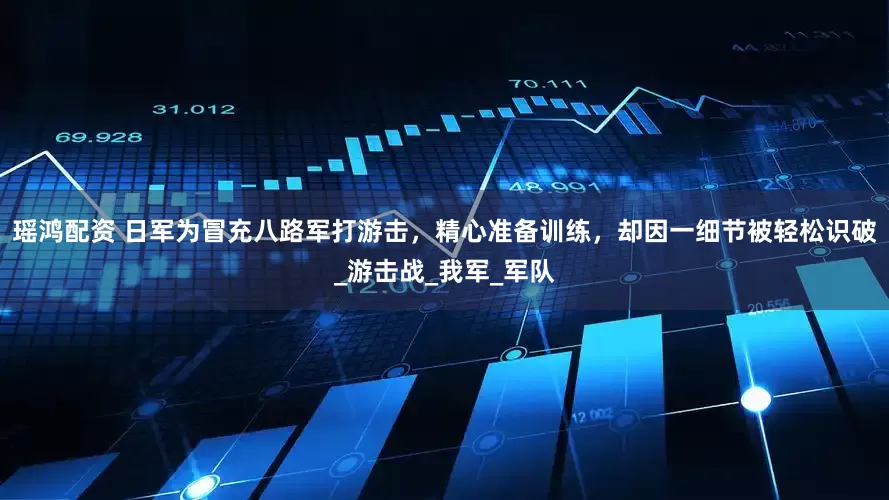
众所周知,游击战术是我军极具代表性的战略手段。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艰苦的环境和强敌,我军正是依靠这种灵活机动的战术,对日军造成了沉重打击,最终成功将侵略者赶出国土。
然而,游击战术的成效显著,使得当时多次受挫的日军也开始重视这种战法,并尝试将其模仿应用于自身部队。可惜,尽管日军经过精心训练,刚一投入实战便被我军敏锐识破,遭到迎头痛击,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
所谓游击战,顾名思义,“游”是指不断移动,“击”则是指打击敌人,合起来即是在不断变换位置的同时,突然袭击敌军,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游击战的历史渊源极为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彼时吴楚两国交战,吴王阖闾采纳伍子胥的建议,派遣多支小股部队对楚国各地进行长时间的骚扰,这种战略消耗了楚军的大量精力,最终在决定性的大战中吴军取得了胜利。
到了汉代,汉高祖刘邦设立了“游击将军”一职,负责指挥对敌的骚扰战术。当时的名将彭越便率领游击军队,专门打击楚军。军事典籍《握奇经·八阵总述》中也对游击战术做出了精准描述:“游军之行,乍动乍静,避实击虚,视羸挠盛,结阵趋地,断绕四径。后贤审之,势无常定。”可见,游击战的灵活多变自古便为兵家所重视。
展开剩余78%尽管游击战术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但真正将其发扬光大、灵活运用并取得丰硕成果的,还是我们八路军。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游击战术就是我军重要的作战方式。那时我军力量薄弱,正是依靠游击战与各地根据地的支持,革命力量才得以不断发展壮大。
抗战时期,游击战术得到了更大规模的应用。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开辟广阔的根据地,发动和武装群众。面对极度匮乏的武器和物资,他们凭借游击战术,在敌后建立起了广袤的战场,对敌军造成了沉重压力。
为何这源远流长的游击战术在抗战时期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并被广泛运用?关键在于毛主席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时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游击战理论和原则。这套理论简洁明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八路军官兵将游击战发挥得淋漓尽致,衍生出“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多种形式,极大丰富了游击战的战术内涵。总的来说,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克服重重困难的情况下,凭借游击战战胜了占我64%兵力的侵华日军和数量更多的伪军,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反观日军,则在我军游击战术的打击下苦不堪言。许多影视作品都有生动展现,当时日军发现八路军难以被彻底消灭,反而越战越强,令其头痛不已,却始终无计可施。
不过,日军内部也有些聪明人。1944年,驻扎山东文登一带的日军,在接连败退、听闻美军可能登陆山东沿海联手中国军队打击他们后,心急如焚。文登,现今威海文登区,距离海岸线较近,一旦美军登陆,日军必然面临严峻挑战。加之太平洋战场的紧张使大量精锐部队被调走,驻守文登的日军兵力捉襟见肘,难以抵挡美军登陆。
面对这一窘境,日军开始冥思苦想应对之策。经过一段时间,终于有一名军官提出不如向八路军学游击战,只要掌握了这种战术,即便美军真的来袭,也能和美军展开游击作战,保存实力等待主力增援。这种想法暴露出日军虽败犹荣的幻想,主力早已被打得支离破碎,却仍在妄图东山再起。
随后,日军以极高的效率展开了“魔鬼训练”,刻意模仿八路军的游击战作风。训练内容包括摒弃汽车等交通工具,选择山地等复杂地形进行长时间的转移和目标袭击演练,力求再现八路军隐蔽迅速、来无影去无踪的战法。
训练一段时间后,日军的行动确实显露出八路军的影子。但这毕竟只是训练阶段,是否成功还需实战检验。于是他们决定派出便衣侦察队,对我军机关实施突袭。
但在实战前,日军意识到形象问题:如果直接出动,因日军普遍身材矮小、行为习惯与中国百姓差异明显,很容易被识破。为此,他们进入第二阶段训练,重点是学习如何模仿中国人的外貌和行为。首先挑选身材较高的士兵,随后找来几个汉奸,在封闭环境下进行严格训练。汉奸教授士兵们如何模仿中国人的说话语调、表情动作,甚至规定不许使用日语。经过数月苦练,这批日军士兵在言行举止上已接近当地百姓,几乎能以假乱真。
训练成果令日军军官欣喜不已,便衣侦察队被派出执行任务。然而,刚出发不久就被我八路军轻松识破并遭到重创,士兵们狼狈逃回基地。
对此失利,日军军官百思不得其解。装扮和举止都已非常逼真,为何还会被识破?调查后才发现真正原因令人哭笑不得:尽管这些“农民”装束破烂,但每个人头上竟然戴着一顶崭新的瓜皮帽。八路军一开始也将其当作当地农民,但看到这些破衣烂衫配新帽子的反差,立刻察觉异常。
为何戴这种显眼的新帽子?原来日军有军规,要求士兵出营必须戴帽穿鞋,不得光头赤足,违反者将受罚。尽管侦察队穿便衣,但长官认为自己依然是正规军,必须遵守此规。但军帽显然不合适,会暴露身份,后勤官员(可能受汉奸影响)便给每人发了瓜皮帽,结果造成尴尬的装扮。
失败后,日军总结教训,决定改进,虽然放弃戴帽,但头上必须遮盖。观察到中国农民常用白毛巾包头,一名军官建议侦察队头裹白毛巾。表面上这个主意细致入微且合理,但第二次行动再次失败。
原因是,虽然包头巾是农村习俗,但主要流行于山西、陕西等地,在文登及山东很少见。带着颜色各异毛巾的“农民”反倒更显突兀,引起了我军怀疑。
更糟糕的是,便衣侦察队成员陆续病倒,高烧不退、腹泻不止,经诊断为伤寒。调查发现,这些毛巾原来是伤寒患者用过,携带大量病菌。毛巾来源是先前的汉奸提供的,而当日军追查汉奸时,却发现他早已神秘消失。
参考资料:《解放文登——伏击战》、《陆军铁帽物语》
发布于:天津市名鼎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